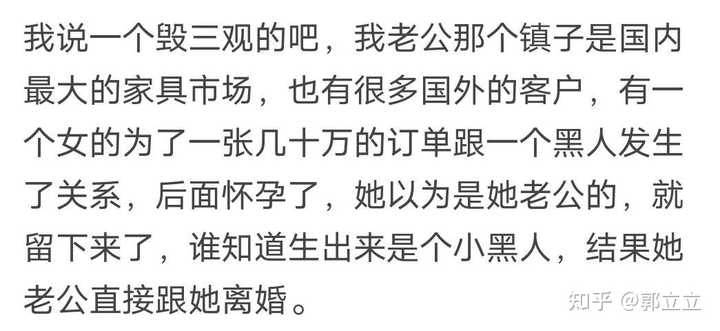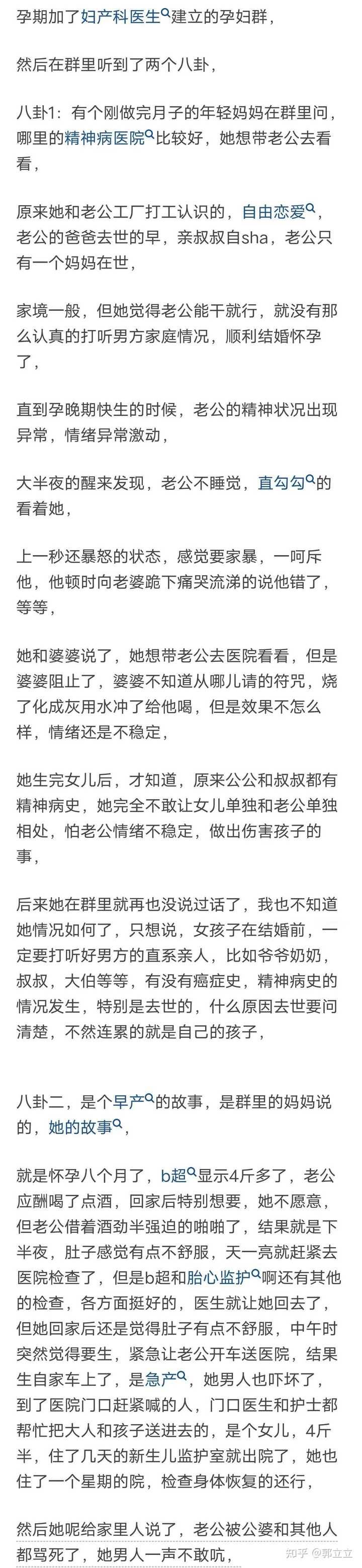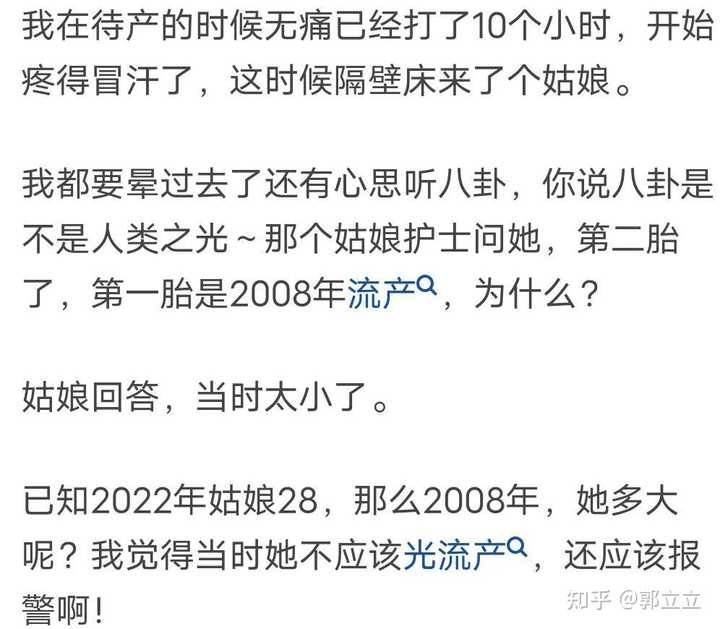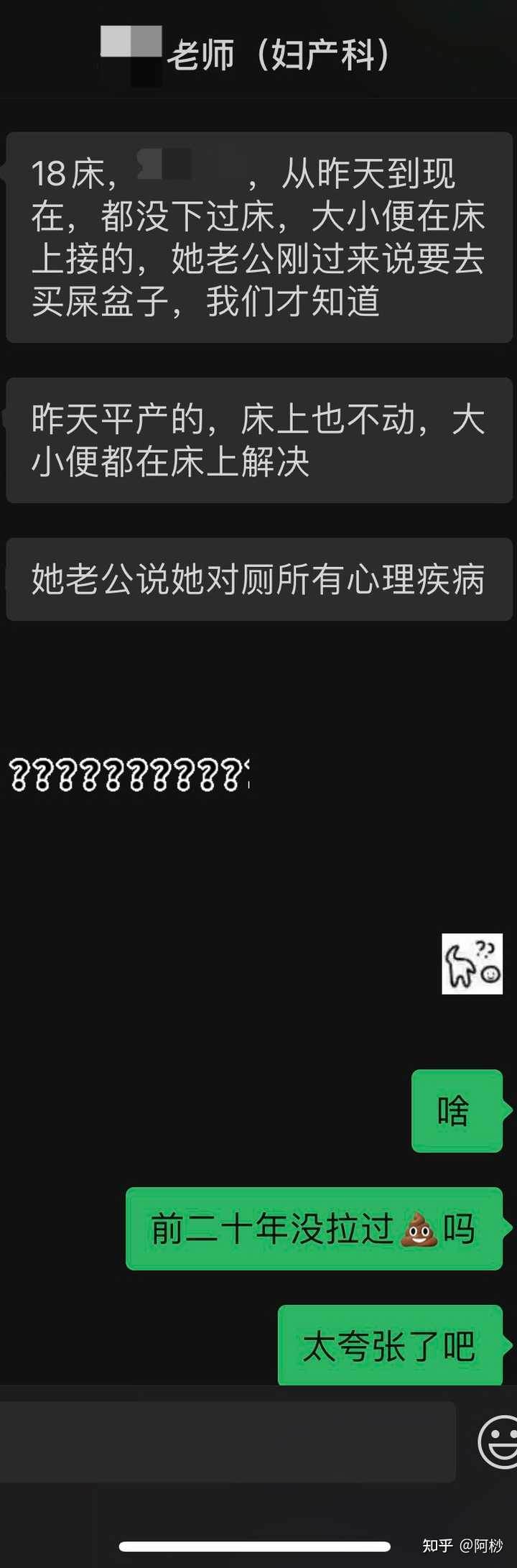一個女孩剛剛分娩,她婆婆就跑來問我:「大夫,多大的孩子能查艾滋?」我愣了一下,她婆婆便告訴我,她兒子有病,害怕傳染給小孩。我簡直怒不可遏:「你明知兒子有病還禍害人家女孩?你要不要臉?」老太婆兩眼一瞪:「那又怎麼了,難道我兒子有病就得絕后?又不是沒掏彩禮!」
1
女孩名叫黨月瑤,二十歲,大學都沒畢業。
她是農村出來的,老家還有一個父親和念小學的弟弟,吃穿用度非常緊張,她只能勤工儉學。
打工的時候,她遇到了一位高中沒畢業但是開著跑車到處收房租的拆二代,懵懂無知的她很快就在對方的熱情追求中敗下陣來。
拆二代立即帶她見了母親,婆婆不但不計較她的出身,甚至很快就安排了婚禮,她還以為自己一直做好事終于撞了大運。
領證前,民政局的工作人員建議兩人婚檢,卻被拆二代拒絕了,他當天就拉著黨月瑤去賓館開房,理由是婆婆急著抱孫子。
不久后黨月瑤就懷孕了,每次婦產科醫生要求她查四項傳染病,婆婆就會帶著她轉院,最后轉了七八家醫院才到我們這來,孩子都足月了。
在得知這個炸裂的事實后,我首先考慮的是醫護安全,于是趕緊跑到產婦病房,把值班護士叫了出來,囑咐她們在護理過程中一定要注意防護。
不出所料,護士們得知黨月瑤很可能感染了病毒,情緒直接崩潰,當場就要求換病房,不行就辭職。
我只好安慰她們:「就算你們走了,也得換其他同事來照顧她,再說,艾滋病沒有那麼易感,只要注意別讓傷口直接接觸到病人血液就行。」
幸好姑娘們都很勇敢,再加上同情黨月瑤的遭遇,她們最終堅持了下來。
我拿臍帶血去做了四項檢測,不幸中的萬幸是孩子健康,她婆婆一直在騙她吃阻斷劑,還說這是進口維生素。
三天后,黨月瑤準備出院,我叮囑她千萬別給孩子喂母乳,她還有些驚訝:「大夫,我感覺胸還挺脹的,為什麼不能給他喂奶呀?」
我嘆了口氣,看來黨月瑤對自己染病的事情仍然一無所知,于是我給她開了一張檢驗單。
我害怕黨月瑤知道事實后會崩潰,就陪她一起去做檢查。不出所料,看到檢查結果后,黨月瑤像瘋了一樣把頭往墻上撞,嚇得護士趕緊叫來了保安。
我想盡各種辦法安慰她:「你也別太絕望,現在艾滋是慢性病,只要按時服藥很多病患都能活得很久。」
黨月瑤悲傷地搖了搖頭:「我只想趁孩子還不記得我就趕緊死掉。」
2
我好說歹說,黨月瑤才鼓起勇氣,帶著剛出生不久的孩子離開醫院。
我擔心黨月瑤會陷入抑郁無法自拔,時常會打電話問候她,了解她的近況,幫她解決一些實際困難。
黨月瑤告訴我,她一離開醫院,就向法院遞交了訴狀,狀告丈夫一家故意隱瞞病情,惡意騙婚,對自己造成了巨大傷害。
可丈夫卻在法庭上矢口否認,他說自己早就告知了黨月瑤自己已經患病,是她貪圖自己家境富裕,所以兩人才結了婚。
黨月瑤拿不出丈夫一家欺騙自己的證據,最后法院僅支持兩人婚姻無效,不支持對丈夫判刑以及黨月瑤的索賠請求,畢竟艾滋病人同樣有權結婚。
黨月瑤絕望透頂,更讓她難受的是,自己的父親居然拒絕唯一的女兒回家坐月子,理由是害怕她把病傳染給弟弟。
她在電話里一邊說一邊哭:「我真不知道自己上輩子到底造了什麼孽,為什麼我要受這樣的苦……」
我心疼黨月瑤的遭遇,于是在院里發起捐款,幫她籌到了兩萬塊錢生活費,暫時解決了一些生活上的困難。
錢的問題雖然解決了,但是另一邊的困難卻讓我束手無策,那就是黨月瑤的婆婆一直在騷擾她。
她告訴黨月瑤:「你沒錢吃藥,很快就會死,這個孩子你養不了多久,還不如交給我們撫養。」
黨月瑤當然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被奪走,于是婆婆用上了各種下作手段逼她妥協。
黨月瑤每搬到一個地方,她婆婆就會立即聯系房東,污蔑她是性工作者還有艾滋病,很多房東當天晚上就會把她掃地出門。
有些房東心善,愿意收留她,她婆婆就會穿上白大褂,偽裝成防疫站的工作人員敲開左鄰右舍的大門,用很大的嗓門喊道:「你們的鄰居是艾滋病患者,請立即到醫院進行體檢!」
不堪受擾的黨月瑤只好再次向我求助,幸好,我有個親戚買了間門面房,位置特別偏僻,一直租不出去,我就把鑰匙借給黨月瑤,畢竟有個屋頂遮風擋雨也好過露宿街頭。
可即便這樣,她婆婆依然不肯放過她,半夜三更偷偷用磚頭把門面房的玻璃門砸了兩個大窟窿。
黨月瑤被折磨得快要撐不下去了,但我一直在鼓勵她。因為我知道,她一旦交出孩子馬上就會尋短見,這個孩子是她活下去的唯一寄托。
與此同時,我對她婆婆的憎惡簡直到了極點,但我卻沒有任何辦法阻止她。
直到有一天,黨月瑤突然給我打來電話:「周醫生,救救我!」
我趕緊開車趕到門面房,只見黨月瑤面色煞白,手里握著一把滴血的大剪刀。
而她婆婆躺在地上,四仰八叉,血流不止,顯然已經死了。
3
我趕緊查看老太婆的脈搏和瞳孔,死了估計有半小時,神仙都救不回來。
她的脖子被撕開一個大口子,傷口處的碎肉很不規則,恐怕是被黨月瑤捅了很多刀。
我問黨月瑤為什麼要做這種事,她非常冷靜地告訴我:「剛才婆婆進屋二話不說就要搶孩子,我不給,她就扯我頭髮拼命打我,還說只要打死我孩子就能判給她兒子,反正她年紀大不怕坐牢。」
黨月瑤忍無可忍,終于爆發,于是就用剪刀殺死了她。
「周醫生,我知道殺人要償命,我也不在乎自己的死活,我就是心疼孩子。一想到他將來孤苦伶仃的,我就想掐死他免得他受苦。可我實在下不去手,我是這孩子的媽啊……」
黨月瑤抱著兒子號啕大哭,她想把孩子托付給我,這樣她也能安心自首。
可問題是,她的前夫還活著,而我只是一個不相干的陌生人,法院肯定會把孩子判給親生父親撫養。
也就是說,自從她的婆婆走進這扇門,這個孩子就注定會被搶走,所以老太婆死的時候才會面帶微笑。
就算法官體恤黨月瑤,從輕審判,那也至少是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,對她來說和死刑沒有任何區別。
我不能讓黨月瑤被捕,絕對不能。
4
我立即返回醫院,取了一套手術工具和兩套手術服,然后從家里抱了四袋貓砂。
「我可以幫你,但是你不能拖我下水,明白嗎?」
黨月瑤立即點頭,她拿出身份證開始錄像:「我,黨月瑤,2024 年 1 月 6 日犯下殺人罪,我發誓此案與周曉蓉醫生無關……」
我雖然不是法醫,但經常做剖宮產,對于人體結構也是無比熟悉。
人體死亡三小時后就會開始腐敗,此時最先變質的是內臟里的殘留物,它們是尸臭的主要來源,只要及時摘除內臟,尸體的味道就會小很多。
我劃開尸體的肚皮,把腸、胃和胰腺依次摘了出來,尤其是能辨認性別的器官,我直接扔進破壁機里攪碎。
黨月瑤在旁邊幫忙,我偷偷觀察她的表情,通常醫學生第一次參與人體解剖都會嘔吐,嚴重的能噁心半個月以上。
但黨月瑤沒有任何不適的反應,她的眼睛里甚至沒有一絲波瀾,仿佛擺在面前的只是一條死魚。
接下來要處理的是骨頭,人的關節極其容易辨認,必須整個粉碎,我沒有那麼大力氣,所以這個過程由黨月瑤代勞,她用小錘和鋸子完成了這項工作。
尸體分解完成后,我用黑色塑料袋連同貓砂把殘骸整個埋了起來,貓砂的吸附性良好,可以避免尸體的味道吸引來野生動物。
至于拋尸地點,黨月瑤決定埋在她母親的墓地里,她母親死于紡織廠火災,老闆為了虛報死亡人數,賠了幾萬塊錢就把她母親的遺骸偷偷處理了,所以這個墓是空冢。
我們挖了一晚上,直到早上七點半,東方天際露出一抹魚肚白,我們才把所有證據銷毀完畢。
黨月瑤的婆婆很早就離婚了,她的兒子最近也不知道在哪里鬼混,所以就算一個大活人突然失蹤,一時半會兒也不會有人發現。
我讓黨月瑤立即搬出門面房,最好離開這座城市,從今往后我們最好不要有任何聯系。
黨月瑤跪下向我磕了三個頭,然后抱著孩子向北離去。
5
為了不引起警方懷疑,我先是安心工作了大半年,小心低調地生活,然后借著進修的機會,調去另外一家醫院的婦產科。
我經常留心網上關于失蹤或者殺人碎尸案的新聞,如果有類似的案件報道,我就會仔細確認細節,直到確認跟我無關后長松一口氣。
為了最大程度降低暴露風險,我在醫院里非常低調,對于別人擠破頭的機會我從來不爭不搶。只要不被人嫉妒,就不會有人對我的過去感興趣。
毀壞尸體的判罰是三年,包庇隱瞞有可能要判三年以上十年以下,假如東窗事發,我肯定是數罪并罰,青春基本要在牢里度過了。
但我一天牢也不想坐,因為我覺得自己沒有錯,該死的不是黨月瑤,而是把她逼上絕路的她婆婆。
至于黨月瑤的命運如何,我雖然關心但從未打聽過,只要警察無法把我們聯系在一起,那證據鏈就不完整,這對于我或者她無疑是最安全的。
我生活得小心翼翼,可最近,我卻接連遇到一些怪事。
首先就是,我感覺有人在跟蹤我。
對方每次會在我下班后跟蹤到我租住的公寓,我不清楚對方的具體身份,但似乎并不是警察。
其次,我經常會收到一些禮物,這些禮物沒有署名,每次都是直接放在我家門口。
禮物有時是車厘子、山竹之類的水果,有時是大閘蟹、龍蝦之類的海鮮,還有一次里面竟然放著一塊「好人平安」的金磚。
為了不被跟蹤,我接連換了三次租住的公寓,可每一次對方都能找上門來,那些禮物也都準時放在門前。
為了搞清楚送禮的人是誰,除夕的時候,我專門出門上班,然后偷偷換了一身衣服回到家里,蹲在門口觀望。
過了一會兒,一個鬼鬼祟祟的男人出現了,他從我門口經過了幾次,然后把東西放在腳墊上準備走人。
我猛然打開門,用掃把指著他:「你是誰!干嗎跟蹤我!我可要報警了!」
男人被我嚇了一跳:「你別激動,我就是警察。」
他從衣服里摸出一張警官證,上面寫著:張澄。
「周曉蓉醫生,我有話要問你。」
6
我瞬間緊張起來。
我不是沒有想過這一天,甚至每天睡前我都會在腦子里排練要怎麼應付警察的質詢,可當真正的警察出現在我面前時,我還是慌了神。
「周醫生,你記不記得一年前曾經救過一個人?當時那個人腹部被刺傷,你為他做了應急處置?」
我張著嘴巴想了半天,旋即回憶起來:那天晚上我剛下班,發現街頭躺著一個渾身是血的黃毛小混混,肚子上插著一把刀,很多人都在圍觀。
作為醫護人員,我對他做了應急措施,然后打了急救電話,僅此而已。
張澄向我敬禮:「我就是那個『黃毛』,當時正在執行臥底任務,如果不是您,我恐怕已經殉職了,今天是專程來向您道謝的。」
他還說,那些禮物其實是他送的,本來醫生下班就沒個準點,他每次在門口等了我好久等不到我回來,就錯過了。
我瞬間松了一口氣,但又有些失望,我本來以為那些東西是黨月瑤送的,但仔細一想,她光是吃藥就要花不少錢,肯定沒有報答我的余裕。
「你要是謝我,直接來醫院給我送錦旗呀,我還能寫個通訊報道呢,干嗎搞得這麼神秘?」
張澄的聲音越來越小:「我怕你有男朋友,所以就跟蹤了你幾天……祝你情人節快樂。」
我這才看清,原來張澄今天帶來的是一束玫瑰和巧克力,他面頰微紅,氣氛變得有些微妙。
我不知所措,但如果不收下張澄的禮物,搞不好他會繼續「調查」我,我可不想承擔這樣的風險。
我接過花和巧克力,問他要不要進來喝杯咖啡,張澄趕緊搖頭,以自己還在執勤為由溜了。
過了幾天,張澄和一個同事抱了一堆關于禁毒的宣傳手冊來我們醫院做宣講,主題是濫用藥物造成的危害。
張澄繪聲繪色地給我們講他在「毒窩」的臥底經歷,他說[毒·品]經常伴隨著艾滋、乙肝等血液疾病傳播,對人民的生命健康造成了嚴重的危害,所以一定要把禁毒進行到底。
院里的年輕女孩子們對聽課沒什麼興趣,注意力基本都在張澄寬闊的肩膀上,一下課,她們就上去問張澄要電話加微信,嘰嘰喳喳。
我拿上筆記本保溫杯準備離開,張澄卻跑到我面前:「周醫生,晚上我們支隊和貴院有個聯誼,我想邀請您一起參加……」
張澄的直男讓我覺得又好氣又好笑,我決定整他一下:「你其實可以單獨約我的。」
張澄大喜過望:「真的嗎?哎,我也不是那個意思……」
我笑而不語,轉身離去。身后傳來同事的閑言碎語:「三十歲的老女人,得意個什麼勁啊……」
使用 App 查看完整內容
目前,該付費內容的完整版僅支持在 App 中查看
??App 內查看